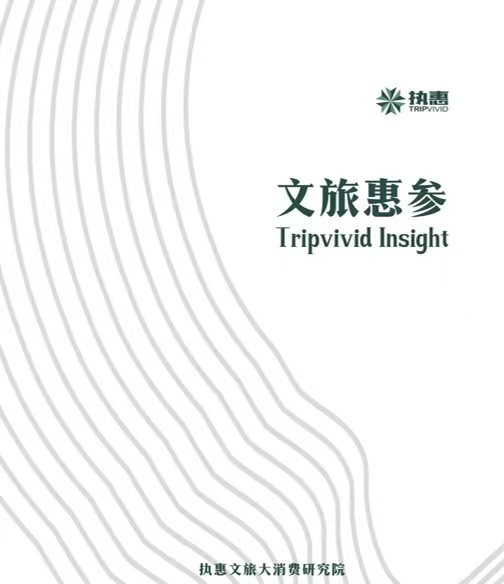新用戶登錄后自動創建賬號
登錄
在2020年接近尾聲時,運營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的日本東方樂園(Orien-talLand)公司在記者會上公布了當年度預計將有約511億日元虧損的消息。受到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影響,東京迪士尼從2月末開始就一直處于長期休業的狀態。7月后雖然園區陸續重新開放,但面對行業協會把游客數控制在疫情前一半以下的嚴格要求,公司最終還是無法扭轉大局。
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東方樂園從1996年上市以來出現的這首次虧損也從側面證明了迪士尼長久以來在日本的超高人氣。事實上,早在園區宣布休業之初就有好事的媒體做過計算:即使從現在開始一直處于沒有游客的狀態,東京迪士尼仍然可以繼續支撐2年左右才會最終倒閉。時任迪士尼全球總裁也曾在樂園開業十周年的活動上說總公司沒有直接經營“東迪”可能是史上最大的決策失誤。他的這個玩笑其實一語道出了“東迪”和其他迪士尼最大的區別。在世界上現有的六個迪士尼主題樂園中,只有“東迪”沒有總部任何比例的持股。除了每年要給迪士尼支付一定的版權費用之外,東方樂園全權承擔園區的建設和運營。這種“本土化”想必也是東京迪士尼可以成為全世界最為成功的主題樂園之一的一大原因。但本文的關心卻并不是作為一個商業典范的“東迪”,而是日本人圍繞著它而展開的一系列言說。作為一個復合空間的東京迪士尼在它誕生的近40年時間里給日本研究者們提供了層出不窮的靈感。而他們的分析不僅把“東迪”變成了一個可供我們觀察日本社會的新窗口,更能幫助我們在全球化仍在推進的當下重新思考權力、資本和文化之間復雜的關系。
戰后的和平“黑船”:東京迪士尼簡史
被人們概稱為“東京迪士尼”的日本迪士尼度假區其實位于千葉縣的浦安市。從東京站出發坐普通電車只要15分鐘就能到達的“東迪”應該是所有迪士尼樂園中離市區最近的了。整個度假區又分為占地51萬平方千米的東京迪士尼樂園(Tokyo Disneyland)和49萬平方千米的東京迪士尼海洋(Tokyo Disney Sea)。根據2019年的數據,前者一整年迎接了1800萬的游客,而后者的數字則達1460萬。如果不算重復而把人次進行簡單疊加的話,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的游客總量甚至超過了美國“本家”的弗洛里達迪士尼,成為世界第一。
而要回顧“東迪”的歷史,不可避免的一個話題正是在戰后日本社會中美國的存在。日本學者吉見俊哉在其著作《視覺都市的地政學》中就專門開辟了一章從此入手。吉見指出,在戰后初期日本民眾對于美國的印象壓倒性地被占領軍所主導。從1950年代開始,這種直接的權力不平等逐漸被一種更為軟化的文化形象所取代。而迪士尼的商業帝國從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57年,著名的百貨公司三越就在其位于日本橋的本店頂層設置了一個名為“快樂的王國迪士尼”的小型游樂園。得到迪士尼授權的包括旋轉茶杯在內的游具成為和父母一起來購物的中產階級孩子的最愛。次年,一檔名為《迪士尼樂園》的節目正式開始在NTV電視臺進行播放。
這一放送周期長達14年的欄目不僅播出最新的動畫還有介紹于1955先行開業的加州迪士尼樂園等環節。這些夢幻的內容對于當時仍在“擁抱戰敗”的日本人來說無疑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世界。有意思的是,吉見指出該節目最早其實和職業摔跤比賽的直播在同一時段隔周播出。而后者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日本的力士們用傳統武術技能擊敗在體格上占優的美國選手。從而,日本在面對美國時“自卑”和“自大”的兩種心態在電視這個媒介上交替出現。
進入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逐漸恢復,日美關系以及迪士尼在日本的角色又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借著日本成長起來的媒體產業,美國文化在雜志、書籍、電影等形式上的輸出更加強烈。另一方面,如果說戰前海軍準將佩里的黑船來航從宏觀結構上促使了日本現代化的話,那么戰后的美國大眾文化則在微觀和日常的向度上改變了日本社會。1971年,麥當勞在日本開出了第一家分店。這種以衛生和效率為代表的標準化餐廳開始讓美式生活方式成為日本人可以切實獲得的物質選擇。這些變化都為迪士尼樂園的最終登陸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從1972年開始,日方代表就頻繁訪美爭取迪士尼落戶。但彼時把心力都投入到剛落成的弗洛里達迪士尼的總公司對于進軍海外完全抱持消極的態度。從而,開頭提到的只提供形象版權而不管經營的方式成為了兩方最終達成的折中。
1981年,樂園破土動工。兩年后的1983年4月15日,“東迪”正式開園。雖然東方樂園公司有著極大的熱情,但起初日本社會對于樂園前景并不看好。園區周邊一段時間內完全無法吸引到住宿業者的投資。畢竟在當時每年要有1000萬游客—相當于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來訪的目標在大多數人看來并不現實。但這些持消極意見的人顯然是小看了迪士尼的吸引力或者說經濟騰飛后日本人的消費力。開園一個多月后的5月23日“東迪”就迎來了第100萬名游客。1984年4月2日,每年1000萬人的目標提前兩周左右達成。此后,伴隨著園區附近希爾頓等高級酒店的開業以及JR東日本鐵道舞濱站的新設等眾多利好,“東迪”的運營就此步上了成功的軌道。迪士尼本身也逐漸沉淀為現代日本大眾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東京灣上的“異托邦”:東京迪士尼的時空策略
除了美國這個重要“他者”之外,迪士尼樂園本身所采取的空間和時間策略也是它可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吉見在書中的觀點,樂園空間最重要的兩個特征在于它的密閉性和平面性。首先,和其他游樂園不同,迪士尼策略性地只設置了一個入口。這確保了游客在園區內會按照管理者事先設定好的邏輯進行“回游”。同時,以交通和金錢為代表的外部媒介都被禁止入園。園內的移動工具只有游客的雙腳和被迪士尼角色所包裹的覆蓋范圍有限的巴士等。而“東迪”直到2008年才開始在園內設置可以使用現金的自動售貨機。就在不久之前,關于能否帶外部飲食進上海迪士尼還成為了一個爭議性的話題。在吉見等研究者看來,禁止外帶等措施與其說是出于盈利的目的其效果更在于排除一切和夢幻的王國無關的物件從而讓游客可以更為徹底地沉浸在樂園之中。另一個有力的例證是,在選址初期日美雙方都曾考慮過把樂園開在富士山腳下。但因為這一日本文化的代表太容易就把樂園內部閉合的故事性打斷,最終漂浮在約等于“空白”的東京灣上的現址才被采納。
自然,樂園空間的第二特征平面性也是為了相同的目標而服務的。吉見認為作為三維空間的主題樂園其終極目的卻是實現迪士尼電影那樣的“二次元化”。比如,園內幾乎所有的建筑越往高層比例越會收縮。這種在動畫中經常會使用的讓房屋顯得立體的手法在真實世界里被繼續加碼。更重要的是,他犀利地指出了在迪士尼內“眺望”這一視角的缺席。雖然“東迪”的象征是位于園區中心的“灰姑娘城堡”,但游客并不能真的登上這一被歪曲了比例的高塔。從而,既看不到樂園之外的現實城市也無法對園區各組成一覽無余的游客能掌握的只有當下所處的游玩平面以及統轄它的童話敘事。
另一邊,與這種空間策略相配合的還有迪士尼園區背后所隱藏的時間意識。在吉見寫作的當時,“東迪”除去入口處的“世界市集”和可以見到迪士尼經典動畫形象的“夢幻樂園”之外,主要的游樂設施分別被安置在從西到東三個主題區域:重現開拓時代美國大西部的“西部樂園”,有加勒比海盜出沒的“探險樂園”,以太空旅行為主題的“明日樂園”。吉見指出這三個部分分別是美國、地球和宇宙三個空間維度上的邊境/前線(frontline)。雖然不同迪士尼樂園下屬的版塊和名稱各異,但這種基本上全球共通的區分早被各地的研究者批判。他們認為隨著游客從印第安人和海盜出沒的前兩個區域來到“未來”時,一種包含了殖民主義的線性時間觀也在潛移默化間融進了人們的思考之中。而迪士尼的這種歷史進步模式其實和19世紀以巴黎和芝加哥世博會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博覽會有著異曲同工的效果。吉見在自己的文章中部分認同了這種觀點,可他同樣也提醒我們注意迪士尼在時間上獨有的復雜性。聯系到上述園區所缺失的能夠俯瞰的制高點,游客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讀懂這種時間的進步是一個未知數。相反的,各種年代可以在同一個空間內共存所帶來的眩暈效果或許才是讓游客能夠進一步放棄日常判斷而陷入陶醉狀態的有效裝置。
迪士尼在逃空間:城市的樂園化及其轉變
雖然密閉性被視為是迪士尼樂園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但顯然“迪士尼式”的空間本身并沒有止步于游園之內,而是逐漸開始占據其他的城市空間。正如鮑德里亞所言,迪士尼樂園的存在是一種為了掩蓋全社會已經完全迪士尼化的不在場證明。
學者北田曉大在著作《廣告都市東京》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十分詳實的例證。在書中,他主要分析了日本零售業巨頭西武集團是如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對澀谷地區進行迪士尼式改造的。集團試圖新建的Parco購物中心因為距離澀谷站有些路程從而讓運營者擔心無法吸引到足夠的客人。而決策者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將街道“主題樂園化”。北田認為這種策略又可以細分為兩層。首先,傳統的街道和街邊市場被積極地吸收進了百貨店內部。不同樓層被賦予了不同的街道主題,而每一層的店鋪又會根據這些主題來進行貨品的選擇和擺設。由此,不怕日曬雨淋更不用擔心商品質量的百貨店成為了一個比日本城市中的商店街還要完美的商店街,就像在“冒險樂園”看到的鱷魚比現實中的鱷魚來的更為真實一樣。其次,公司更把野心投射到了百貨店之外的城市全體。從澀谷站周圍延伸到Parco的各條道路也被按照一定的主題進行劃分。比如在“西班牙坂”附近的店鋪不管是裝潢還是提供的食物都讓人有置身馬德里的錯覺。而不論大樓外墻還是引導標志,只要是行人所見之處都被公司精心挑選的符合“Parco審美”的商品廣告所占據。可以說,顧客一下車站就進入了一個看似開放其實早被商業資本環閉起來的主題樂園之中。和在“東迪”一樣無法俯瞰內外的消費者只有主動融入其中并進行符合這一空間的消費行為才能達到沉浸式的滿足。而他們穿在身上的衣服,口口相傳的電影或展覽又成為“二次廣告”繼續再生產出沒有縫隙的消費樂園。
隨著整個城市被一個個“小迪士尼”覆蓋,無處可去的消費者只能—其實更多的時候是主動—投入到沒有出口的商業迷宮之中。可就像迪士尼故事沒有告訴觀眾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之后可能會經歷的滿地雞毛,看似完美的樂園型消費城市很快也迎來了新的轉變。如果說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迪士尼式的空間從游樂園逃竄到了城市中,那么從1990年代開始我們見證了“東迪”空間對自身的逃離和瓦解。
曾經在迪士尼做過兼職的學者新井克彌在《迪士尼的社會學》一書中詳細記錄了被他稱作“脫迪士尼化的東京迪士尼”現象。其中,2001年東京迪士尼海的開幕是一個最明顯的指標。首先,迪士尼海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封閉自己的空間。甚至能從園內觀賞東京灣和遠處的城市變成了樂園的一個賣點。其次,園內打破了世界各地迪士尼為了營造家庭共樂的氛圍而嚴格禁止的酒精販賣。雖然各色飲品還是被起了迪士尼式的夢幻名稱,但當你身處迪士尼海的餐廳內不時會有誤入東京巷子里某間居酒屋的錯覺。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新井評論道這些變化背后的共通原因都是因為“東迪”的主題性開始變得越發稀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迪士尼的代表性活動—歡樂大游行。新井指出在1980年代,“東迪”的游行都有著十分明確的大主題,而每個彩車和方陣又有著完整的故事設定。但1990年代之后一種混沌感卻籠罩了表演隊伍。不僅不是一個故事內的人物被隨意安排到一輛彩車上,有些根本和迪士尼無關的形象也同時出現在表演者和觀眾兩方的身上。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混亂卻讓來客體會到了全新的娛樂感。他由此提出傳統的自我完結性主題在世紀之交后逐漸失去了吸引力。隨著網絡等新媒體的發達,游客們身體和心靈的“在場”十分容易就實現分離。由此,再試圖把他們困在一個由完整故事覆蓋的空間內變成了不可能實現的妄想。正確的解決之道是提供盡可能多樣和多量的信息源讓游客個人可以從中找得到自己想要的片段進行DIY組裝。比如喜歡《冰雪奇緣》的人早在網絡論壇知道了“東迪”的哪個商店有艾爾莎的周邊而第幾輛花車又有姐妹兩人的團圓場景。
同樣,“東迪”這種閉合“信息繭”的破裂在實際的城市空間中也能找到對應。再回到北田曉大筆下的澀谷。一樣從1990年代開始,西武的“城市廣告化”策略也開始出現裂痕。雖然人們繼續聚集到到澀谷,但他們的理由不再是尋找“澀谷系”的商品,而是因為澀谷有足夠多的商品所以他們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從澀谷站到Parco百貨店的路上,建筑外墻曾經充斥的西武系固定廣告牌紛紛被能實時反映流行動向的電子顯示屏所取代。但這些研究者也都提醒了我們,如果要就此認為大資本試圖控制城市和消費者的努力失效了的話不免有些天真。事實上,自我完結性被打破后的“東迪”相比于仍在堅持正統夢想王國的美國本家運營看似更為順利。東京迪士尼海陸續推出的原創形象不斷受到歡迎甚至轉銷海外,而整個園區游客的回頭率和人均消費額也一直都處在上升的態勢。
尾聲
盡管因為疫情的原因,“東迪”首次出現了經營虧損,但運營方和市場顯然絲毫沒有降低對它前景的看好。重新開園后的9月28日,橫跨了三個園區(再次打破完整性!)投資了近750億日元的大改造正式開始迎接游客。此外,面積達到14萬平方公里總額預估2500億日元的新項目也將按照疫情前的計劃動工。如果不把眼光限定在迪士尼,包括環球影城下屬的任天堂世界,吉卜力公園,哈利·波特樂園等數個大型主題游樂項目現下也正在列島上同時動工。在已經完成后工業轉型的日本,跨國資本和本土文化又會帶來什么新的消費習慣和空間實踐?而普通民眾的能動性甚至是反抗又將有什么不一樣的發展?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管是作為前車之鑒還是他山之石一定會給其他社會帶去不一樣的啟示。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經濟觀察網”(eeojjgcw),作者:黃秋源,原標題:《日本迪士尼:一座后現代社會傷疤上的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