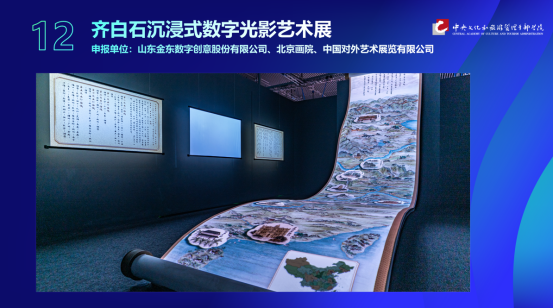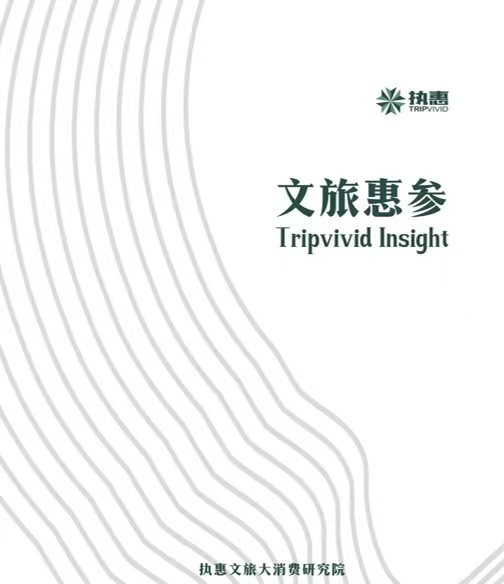新用戶登錄后自動創建賬號
登錄
最近朋友圈又被共享單車刷屏了:繼上海大叔把摩拜扔進黃浦江之后,網友們紛紛曬出各地共享單車被拆卸破壞、被改頭換面加上私鎖變為己有、被強行圈地收管理費、被亂停亂放阻塞交通的照片,并表達了對國民素質的擔憂,甚至有人長嘆:中國人不配使用共享經濟。但這些奇葩行為很多已經超出道德范疇,屬于違反交通規范和社會治安管理法,是法律層面的追懲問題(侯虹斌)。也有人不同意國民素質論,立足點卻是資本有力量,不需要政府和公眾監管,靠公司創新就能解決(新京報)。
在這場國民素質大討論中,不論正方還是反方,都將共享單車服務視作進步力量,卻較少有人對共享經濟本身存在問題的反思。從摩拜單車被人為損毀和拋擲、Airbnb住房被租客粗暴對待等等社會新聞報道中,似乎只能看到,傳統行業的因循守舊和普通個體的“素質低下”,并且往往以前者的保守落后來體現“共享經濟”的進步文明,但唯獨欠缺對“共享經濟”背后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如胡凌所說,“共享經濟”這個概念本身已經被意識形態化了。Airbnb短租、摩拜/ofo單車、優步/滴滴打車、58快運/貨拉拉等一撥以調用配置線下物質資源的互聯網企業無論是在當下的新聞報道還是街談巷議里都被視作典型的共享經濟。但這里的“共享”得打上雙引號:因為共享并非共同享有或者免費享受,用戶/消費者是通過企業打造的互聯網平臺資源配置,按市場價格付費獲得私人汽車、單車、住房以及其他物質資料在一段時間內的使用權,而非所有權。

被故意損壞的單車坐墊
祛魅“共享經濟”:自由分享話語掩蓋了消費者作為免費數字勞工
經濟的本質是社會交換。美國法學教授勞倫斯·萊斯格指出,人類社會的兩種基本經濟模式是商業經濟和共享經濟。商業經濟作為交換對象的是可見的物質形式,例如金錢、有形資產等等;分享經濟則是基于社會互動的日常實踐,交換的是不可見的社會價值,例如情感、人際關系、集體認同、名聲等等。商業經濟是資本市場的運作方式,而我們所理解的公共生活和社群共同體則是建立在共享經濟的基礎上:朋友之間分享書籍、電影和音樂,并不需要向對方付費;同事開順風車捎上你,也不需要你為之買單;《星球大戰》粉絲基于對電影的狂熱而私下創作衍生作品,沒有從中獲得任何金錢報酬。這些無法被簡單化約為市場經濟的社會交換,我們稱之為共享經濟。互聯網的技術革新帶來新經濟模式:當線下日常生活的共享經濟模式遷移到線上,例如書籍、電影、音樂的共享,則為互聯網公司免費提供了生產資料用于商業經濟,就連用戶的個人資料和上網行為的收集、研究和利用本身也包含了巨大的商業利益。這種商業經濟與共享經濟之間邊界的模糊和模式的混合,被稱作互聯網時代所造就的第三種經濟形態:混合型經濟(Hybrid economy)。萊斯格也只是止步于指出混合經濟的巨大商業潛力,而沒有對混合型經濟背后的權力運作展開批判性分析。當下火熱的共享經濟絕非字面意義上的共享經濟,實則是混合型經濟。 “共享經濟”與其說這是互聯網公司的運作模式,不如說是推銷給用戶的價值觀,用以號召和動員消費者自發自愿地貢獻時間、精力、資源和數據為己所用的營銷策略。這套具有濃厚后福特主義色彩的自由分享話語掩蓋了消費者作為數字勞工與企業平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權力不平等。
以網約車為例,早期滴滴、優步通過平臺算法優化配置私家車資源、打價格戰吸引消費者紛紛轉向網約車服務,但當燒完風險投資可以提供給司機和乘客的補貼,滴滴又合并了優步形成行業壟斷之后,價格就會隨公司意志而調整提高,正如現在很多人的切身感受:滴滴打車越來越貴,還不如出租車。當遇到交通高峰期,不加價就根本打不到車,最后就是誰有能力付更多的錢誰才能打車。平臺規則完全由公司制定,既沒有經過政府監管,也并非司機和用戶可以議價。而傳統出租車行業因為有物價局的定價標準,所以提供價格相對穩定的租車服務。傳統出租車公司的人工成本還包括司機的五險一金,司機需要向公司繳納“份子錢”獲得運營執照,出租車公司也與保險公司有著固定的保險理賠合同,一旦發生交通事故,乘客可以直接向出租車公司理賠。而滴滴從早期以私家車車主、傳統出租車司機為主的個體化運營轉變為公司大量購車招募全職司機的公司化運營,不斷通過靈活分散的租車服務外包繞開了這些人工成本,將過去的“黑車”納入平臺信用評價與活動積分的游戲規則。但同時卻沒有提供雇員與傳統租車行業相同的社會保障,全職司機隨時面臨被解雇的風險,全職司機絕大多數為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外來流動人口。香港中文大學一項針對全國出租車司機的問卷調查報告顯示,網約車服務并沒有改善司機的勞動狀況,反而是減少了收入(42%),加大了工作強度和工作壓力(57%)。因而可以說,消費者和司機都只是在剛開始可以從“共享經濟”中分得短期紅利,但長期以往,網約車公司的目標是擊垮并取代傳統出租車行業,重新洗牌和制定行業規則。全職司機的社會勞動保障制度將因為傳統出租行業的衰落而面臨崩塌,消費者個人也面臨交通成本增加打不起車的困境和遭遇交通事故難以索賠的潛在風險。打著“共享經濟”的網約車利用靈活用工和勞務外包,規避政府管制的方式最大化平臺自身的商業利益。
除了勞動者的社會福利和消費者的安全保障的缺失之外,不為人注意的是,用戶和司機還是公司平臺的免費數字勞工。信息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就是信息本身,而司機和用戶使用平臺產生的數據就是產品,而這些勞動被企業以優化服務的名義無償占有、使用和營利。當下的大眾媒體報道卻都指向傳統行業的保守落后和司機、消費者個人的“素質低下”,為新經濟的長驅直入提供合理性,卻無視其對勞動者權益的強制削減和對消費者數據的無償使用,鮮有對互聯網企業的數據搜集與監控、消費市場調查、廣告營銷公關等信息管理與控制活動的描述。對于“共享經濟”的企業而言,最大的財產不是房產、汽車、自行車等物質資料,而是龐大的用戶基礎和生產的數據,通過調配跨區域的個人需求和物質資源來完成,而這些必須依靠用戶的主動配合和使用,這些由分散個人無償提供的時間、注意力和數字勞動被視作理所應當,而用戶數據庫具備重要的市場調研和營銷推廣價值,技術則增強了企業對市場的科學管理,通過刺激需求、記錄品味和監督消費等等技術手段來作為企業市場決策的重要依據,建立更為有序和可控的市場環境,因而在用戶個人看來似乎無足輕重的信息(這些信息被抹去個體痕跡而作為消費者群體特征被使用,與我們通常理解的“隱私”是不同的概念)被大規模收集之后就有著極為重要的經濟價值。而被無償使用信息的個人往往沒有拒絕企業隱私搜集的選項(opt-in/opt-out),也不具備對信息如何被監測、搜集、使用和販賣的知情權。在大數據的收集和分析中,人自身日趨被降低到數據的地位,成為企業監測、分析和計算的對象。信息技術升級了信息資源所有者(公司)對信息搜集和積累的能力,推動對信息更有效的集中和系統的壟斷,讓數據監控無所不在和無時不在,但公眾卻沒有獲得同等的監督權利和制衡籌碼。其次,“共享經濟”也存在對使用者的時間和空間的殖民。時間的殖民化意味著用戶在工作以外的閑暇時間也在這種資本邏輯支配下變相成為一種消費“勞動”,人們使用軟件打車自助式完成接單、溝通、評價與結單的行為大大節省了公司的人力資源成本。空間的殖民化則是指新技術打破傳統租車行業的集中管理和準入標準,給用戶帶來表面上更多的選擇和自由,但離散化并不意味著走向自由民主,而是優化和精簡了控制權力的有效行使。如我們所見,滴滴合并優步繼而采用全職雇傭司機的策略,公司運營將進一步集中化和一體化,所謂的離散化和個體化只是使用權力在普通用戶和兼職司機群體中的組織形態。
當然很多人對所謂的“共享經濟”有著方便、快捷、低廉的良好使用體驗,并且主動認同于這些企業的品牌宣傳話語,這和企業平臺對用戶信息與活動數據的無償占有和利用并不矛盾,也恰恰因為前者,后者容易變得隱蔽而難以察覺,甚至因為“搜集是為了優化服務”而獲得正當化。耐人尋味的是,跨國IT企業非常擅長本土化包裝,例如作為營銷策略推出的 “人民優步”,實質是利用平臺優勢調動和配置私家車資源,提供用戶有限的使用權。“人民”的實際所指是自由市場上的消費者和私家車租賃者,“人民優步”似乎也給網約車抹上了天然的道德正當性,暗示反對的聲音是腐朽的、落后的、糟糕的“敵人”。與此同時,優步在西方國家進行媒體公關的話語策略卻是巧妙挪用“民主”一詞,將消費者與政治選舉的投票人悄然劃上等號。而這兩種話語都意味著將企業等同于社會,無論是“人民”還是“公民”。反對新經濟,就是反對社會,就是與“人民”/“公民”為敵。
祛魅“國民素質論”:不配合新經濟就=不具備現代公民的基本文明素養?
信息革命往往被定義為提高人類智力水平、改善日常社會生活、拓展人類對現實世界的掌控能力等等光明前景,技術的黑暗面和消極影響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共享經濟”所仰仗的一套意識形態是,信息技術是進步的社會力量,而一切對于技術的拒絕和惶恐都是落后、愚昧和不識時務。國民素質論的甚囂塵上則延續這一線性技術進步論的邏輯:反對或者不配合新經濟就是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不具備現代公民的基本文明素養,是粗鄙、低素質、不配使用新科技的“游民”,甚至將這些社會現象上綱上線到對中國人整體素質的批評。一方面,將反對者開除出現代社會生活的公民群體,另一方面則暗示技術推動者(互聯網企業)是復興公共生活的希望。輿論一邊嘲笑“低素質”人群拒絕適應和使用新技術是多么可鄙和迂腐,一邊暗示新經濟能夠讓我們回到田園牧歌式的理性公共生活。
可是公共生活何曾是建立在市場之上?即使在歐美語境里,國家、市場和社會也是互相獨立的三角關系,社會與政府和市場兩者截然區分,市場從來不意味著公共性,相反公共領域要時刻警惕市場對其的侵蝕。在國民素質論的討論浪潮中,曾經作為政治概念的“人民”被挪用為網約車的商業模式搖旗吶喊,公共性也被偷換概念和簡化為市場交易過程中的個人素質和社會信用問題,并且部分人提出的解決方案之一竟然只是將用戶而不包括這些信息權力過于龐大的公司列為監管對象。企業對個人資料和使用行為的搜集、記錄、分析和利用的權力邊界有誰來制約?究竟誰才是破壞線下公共生活的主角?誰才應該接受公眾的監督呢?
我們對于新媒體技術的認識仍然沉浸在浪漫迷思中:科技是解圍之神,它將改變一切,且將順著好的方向發展,只要我們聽從它的召喚。這套論述的主要觀點包括:技術必然是有益的;技術是中立的,它本身不具有價值取向,關鍵在于人們如何利用它;技術進步是社會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而很多研究者已經認識到,將信息革命僅僅作為純粹的技術創新來理解非常幼稚,它們實則抑制和遮蔽了存在于信息技術運作背后復雜的權力關系和結構性的政治經濟力量。要理解信息技術的社會影響,必須考察信息技術與資本市場、國家政經制度、產業所有制結構、代碼空間的權力架構之間的關聯。對于歡呼信息革命的技術樂觀派而言,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市場機遇和新技術帶來的商業潛力。對于他們而言,要的不是公共性,而是以公共性為名號召大家為新經濟免費打工且樂此不疲。而新盧德主義者對此的回答是拒絕。
*本文轉載自《和訊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