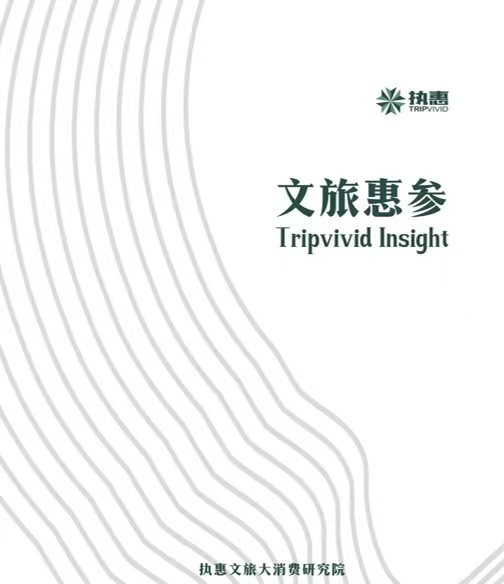新用戶登錄后自動創建賬號
登錄
2020年3月,距離埃航737Max飛機墜毀已經過去整整一年,波音——這家全球工業制造明星——依舊未能走出丑聞,全球禁飛737Max讓它至少損失180億美元,股價從空難前最高的440美元/股暴跌至現在(3月6日)的262美元/股。
此前的1月,波音沒有獲得任何新飛機訂單,系58年來第一次。
這是波音因“短視”而付出的代價。
波音管理層不愿在產品研發上投入重金,過去20多年推出的唯一一款全新飛機是787,最近十多年再無新機型,而連續出事的737Max幾乎是被競爭對手空客倒逼的結果。
在波音董事會上,謀劃多年的NMA項目(New Midsize Aircraft)像皮球一樣被踢到現在,仍然沒有下文。相反,競爭對手空客去年推出的A32lXLR已經拿下超過450多架意向訂單,在這個細分市場已經領先一大步。
波音更樂于在股票和利潤上做文章。過去6年(2013-2018),波音董事會毫不猶豫地拿出407億美元用于回購公司股票,又拿出161億美元用于股息分紅,而同期用于商用飛機的研發投入只有141億美元。
在股票回購等手段刺激之下,波音股價翻倍上漲,理論上符合“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美國公司治理宗旨,但獲利最大的卻是華爾街投資者和波音的高管群體。
從“工程師公司”到華爾街寵兒,波音的轉變肇始于23年前,那場航空業世紀大并購。
麥道“收購”波音
1997年,波音以133億美元收購了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簡稱“麥道”),這場世紀并購被認為是波音走向平庸的起點。
當時的波音已經是全球航空業霸主,在民用飛機領域的市場份額達到60%,短板在于軍事業務,這部分收入約占公司收入的兩成,相當于麥道的一半。
麥道曾經是美國最大的軍用飛機制造公司,該公司約七成利潤來自于軍事部門,但在客機領域的競爭中不斷敗給波音和空客,被波音兼并之前的全球市場份額萎縮至僅剩5%。
1996年11月,在美國新一代戰機“聯合攻擊戰斗機(JFS)”的競標中,美國國防部宣布將從洛克希德-馬丁和波音兩位死敵中選擇,麥道鎩羽而歸。
軍民兩大市場紛紛敗北,麥道選擇“賣身”。
波音當時面臨著來自于大西洋彼岸的挑戰,1970年成立的空客在客機領域已經搶下全球35%的市場份額。波音通過并購麥道不僅能在技術和資源上實現優勢互補,同時還能斬斷空客與麥道攜手的可能。
麥道的江河日下客觀上促成這筆交易。1997年,在重組后的新波音董事會中,三分之二的董事來自于波音,三分之一來自于麥道。
在執行層面,來自波音的菲利普·康迪特擔任新波音CEO,主要負責公司戰略規劃;來自麥道的哈里·斯通塞福擔任總裁和COO,負責日常經營。
表面上“波音人”控制著新波音的董事會和戰略執行。
《巨無霸:波音747的勝利》一書的作家Clive Irving對此的評價是:“本應該是波音接管麥道,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這是致命錯誤。”
對于這次并購,波音前商用飛機部門總裁羅恩·伍達德2007年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原本以為波音會趁機殺了麥道,但根本沒有,“我認為哈里比菲利普更聰明,他和他的團隊用波音的錢買了波音。我們都覺得非常惡心。”
麥道“并購”波音的案例,已經出現在《企業兼并與收購案例》等高等學院經管專業的教科書中。
這本書中提到一個細節:波音當時有一個18人組成的高管團隊,其中7人來自麥道,1個人來自波音,其余是從外部請來的職業經理。
波音“變味”了
波音以精湛的工程技術聞名于世,開創了噴氣機時代,陸續打造出707、737、747、757、777等暢銷機型,逐漸確定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這一切除要感謝美國政府補助之外,還要歸功于波音工程師將設計和質量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堅持。
合并麥道之前,波音的員工傾向于將公司視作一個由龐大工程師群體組成的“大家庭”,互相之間可以平等對話,但哈里和其他麥道高管的強勢入主改變了這一切,他們認為工程師“傲慢自負”。
哈里對員工說:“不要再和以前一樣像個家庭,而是要像個團隊。如果有人在團隊里表現不佳,就不配留下來。”
“有人說我改變了波音的文化,這正是我的目的。這樣一來波音才能像公司一樣運作,而不只是一家優秀的工程公司,因為股東投資公司就是為了賺錢。”哈里2004年在接受《芝加哥論壇報》采訪時表示。
某種程度上,哈里想要改變波音的企業文化是為了應對市場競爭,這一改變得到CEO菲利普和董事會的支持。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在卡特和里根兩任政府的支持下,長期受政府管制的航空業得以松綁,準入門檻被降低、價格管制被放開,催生出一大批新的航空公司。
與此同時,航空公司之間的價格惡戰日趨激烈,導致他們無法再和過去一樣將購買飛機的成本通過票價轉嫁給乘客,他們要求上游的飛機制造商降低成本。
如此一來,波音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不計成本地研發一款新飛機,比如當初押上公司身家性命的波音747。再加上來自于大西洋對岸空客的挑戰,波音愈發重視成本和利潤。
哈里是一位精明的職業經理人。在進入航空業之前,他在通用電氣(簡稱“GE”)工作超過25年,后來將GE已故CEO杰克·韋爾奇提倡的“股東利益最大化”理念“完美”復制到了波音。
合并之后,波音管理層宣布削減麥道兩款民用機型MD80/90的生產規模,同時進行大刀闊斧裁員,當時的計劃是到1998年時將民用飛機部門的崗位削減1.2萬個。
該舉動引發了員工的不滿,并且伴隨著兩種企業文化的反復博弈,這種情緒在2000年到達頂峰,導致了一場持續時間長達40天的大罷工。
員工們覺得波音“變味了”。
成千上萬名“波音人”走上西雅圖街頭,除了抱怨收入不如亞馬遜等互聯網新貴公司之外,還將怒氣撒在哈里身上,覺得他和其他來自麥道的高管改變了波音親如一家的工作氛圍。
“波音過去崇尚的質量優先、強調溝通的企業文化被遺棄了。相反,麥道‘利潤至上’的價值觀被帶到波音,并在波音生根發芽,最終成為主流。”跟蹤波音幾十年的美國航空業分析師、Leeham公司總經理Scott Hamilton告訴《棱鏡》。
離華爾街更進一步
2001年,波音做了一個更大膽的決定,將總部從西雅圖搬到芝加哥。
CEO菲利普·康迪特給出的解釋:“當總部位于主要業務附近時,公司的重心難免會被牽扯進日常的業務運作中”。
當時的波音不再是一家簡單的客機生產公司,在合并麥道之前,波音還收購了羅克韋爾公司的防務和空間業務,成為一家橫跨客機、軍機以及航天業務的國際巨頭,年收入超過500億美元。
芝加哥位于美國中東部,交通網絡發達,是波音大客戶美國聯合航空的總部所在地,距離西雅圖工廠2000多公里,距離華盛頓和紐約只有一個小時的飛行時長,方便波音高管前往五角大樓進行游說,以及博得華爾街的歡心。
當時負責波音新總部選址的John Warner曾對《經濟學人》雜志表示:“新總部可以讓華盛頓的政府官員和紐約的金融市場更容易接觸到我們。”
Hamilton認為總部搬遷客觀上降低了工程師和管理層之間的溝通效率,“但如果考慮到當時波音的軍事業務正在增長以及公司的財務導向,這么做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過,美國獨立航空分析師Alex Lee則對《棱鏡》表示,像波音這樣的大公司向華爾街靠攏并不百分之百是一件壞事,“這要看它做了什么,以及沒做什么”。
與華爾街越走越近的波音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波音和麥道的合并發生在1997年。當年美國資本市場出現了一個轉折點:股票回購的數額超過公司現金分紅。
同樣是1997年,美國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第一次明確表示:將‘股東利益最大化’作為公司治理的宗旨,這一聲明對資本市場產生深遠影響。
成立于1972年的美國商業圓桌會議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商界組織之一,1978年開始定期發布與公司治理原則相關的聲明,高層成員包括蘋果、沃爾瑪、GE、摩根大通、IBM等頂級公司的CEO。
“不少麥道高管都在GE工作過,他們入主波音之后,在內部推行股東利潤最大化策略,包括大規模的股票回購(除了現金股利),以及將生產環節大量外包。”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教授William Lazonick告訴《棱鏡》。
Lazonick教授長期研究產業競爭力。他撰寫的《創新魔咒:新經濟能否帶來持續繁榮》 的一書2010年獲得熊彼特獎。
合并麥道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8月,波音宣布了一輪股票回購計劃,規模達到流通股的15%。按照當時的股價,這批股票價值約45億美元,超出波音連續兩年的凈利潤總和。
財報顯示,1998年和1999年,波音的凈利潤分別是11億美元和23億美元。
股票回購作為一種刺激股價上升的常規手段,理論上可以讓所有公司股東受益,但獲利最大的卻是華爾街的投資者和波音的高管群體。
例如,公開資料顯示,在1997年合并之后,一直到2005年被迫辭職,哈里一直是波音最大的自然人股東之一。
暴漲的股價與高管薪資
經歷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波音的股票回購計劃卷土重來。
財報顯示,2013年,波音用于股票回購的金額為29.01億美元,之后一路上漲到2018年的90億美元。換言之,過去6年時間(2013-2018),波音花在股票回購上的資金達到驚人的407億美元,平均每年為67.7億美元。
此外,從2013年第一季度到2019年第一季度的6年時間內,波音的現金股息分紅累計達到174億美元,相當于同期利潤總額的42%。
在這6年周期內,波音用于商業飛機的研發投入累計為141億美元,只有股票回購規模的三成,連年少于股息分紅,平均每年的支出約23.6億美元。
《棱鏡》根據波音財報統計還發現,2014年開始,波音把92%的經營現金流用于現金股息分紅與股票回購。
波音股價不斷上漲,2019年3月埃塞航空難發生前一周,創下歷史新高的439.96美元/股,相當于2014年年初的3.5倍。
就在印度尼西亞獅航發生第一起737Max墜機兩個月之后,波音董事會還批準了價值200億美元的股票回購方案,計劃兩年之內完成,后因埃塞航空難和737Max停飛被迫中止。
Lazonick教授2014年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過一篇名為《Profits Without Prosperity》(只有利潤,沒有繁榮)的文章,“美國大公司的高管沒有將利潤投入到創新和提高生產效率上,而是用于大規模地回購公司股票。”
該文章一組數據顯示:“從2003年至2012年,標普500指數中總共有449家上市公司一直處于掛牌狀態。在這期間,他們將公司利潤總額的54%,共計2.4萬億美元用于回購自家公司的股票,而且幾乎都是通過公開市場交易,還有37%的利潤用于支付股息,最后只剩下很少一部分用于提高生產力和員工薪酬。
“在公開市場中進行股票回購的唯一目的就是刺激股價。公司高管有動力這么做,因為他們的工資往往與股價以及公司利潤掛鉤。”Lazonick告訴《棱鏡》。
波音股價與高管(尤其是CEO)收入呈正相關關系。
財報顯示,以2005年-2015年擔任波音董事長和CEO的吉姆·邁克納尼為例,2014年他從波音賺走2900萬美元,只有200萬是基本工資,其余都是與業績表現、股票期權掛鉤的獎勵,在任的最后三年時間內,他又從波音賺走大約7960萬美元。
邁克納尼的繼任者丹尼斯·米倫伯格2018年從波音拿走2340萬美元。雖因737Max安全性丑聞在2019年年底被解雇,但按照合同,他還是可以繼續拿走6200萬美元,包括養老金和現金激勵(不包括價值上千萬美元的股票期權)。
接替米倫伯格的是之前在GE任職26年之久的大衛·卡爾霍恩,他的上任并沒有打破這一發薪規律。
根據波音2020年1月披露的資料,新任CE0今年的基本工資為140萬美元,以及250萬美元的現金獎勵。如果他可以讓737Max順利復飛,那么可以獲得另外700萬美元的獎勵。除此之外,還有價值1000萬美元的受限股票。
麥道的老路與教訓
“華爾街的投資者當然喜歡股票回購,股價上漲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問題在于,資本市場是短視的,一切都是關于下個季度或者下個財年,然而航空業需要看得非常長遠。”航空分析師Alex Lee告訴《棱鏡》。
“如果保證后續的合理投資,一個機型系列通常可以生產50年以上(波音737就是這樣)。如果你的眼光只停留在未來一到兩年,那么你可能不會投資一兩百億美元打造一款新飛機,因為這可能需要十幾年才能收回成本。”Alex進一步解釋。
737家族是波音的王牌產品,也是全球航空業有史以來最暢銷的客機,首架737-100于1967年首飛,1968年開始投入服務,1996年推出家族的第三代產品NG系列。
進入21世紀,737NG系列到了更新換代的關鍵時期,此時的波音管理層并沒有及時將錢投入到新機型的研發。
公開資料顯示,從2004年到2008年,波音共計斥資約110億美元用于股票回購,“如果用這些錢來打造一款全新飛機替代737NG,綽綽有余。”Lazonick對《棱鏡》表示。
波音管理層對于推出一款新飛機取代逐漸老去的737始終猶豫不決,直到對手空客搶先一步推出新一代A320NEO,并從波音最忠誠的顧客美國航空手中拿下260架訂單時,波音匆忙應戰。
波音的決定是,在已有的生產平臺上推出737家族的第四代產品Max系列,僅用三個月時間就拿出改造方案。
為在燃油效率上和空客對抗,737Max換上了更大、更省油的發動機,但因機身的限制,發動機被迫往上前提,這導致飛機在起飛時可能有失速風險。波音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在飛機上安裝傳感器來判斷飛行過程中是否抬頭過高,通過MCAS(機動特性增強系統)避免飛機俯沖。
這套MCAS系統并沒有讓飛機更安全,恰恰相反,根據目前的初步調查結果,傳感器讀取數據錯誤引發的MCAS系統失靈,被認為是兩起空難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
這兩起空難共造成346人死亡。
Alex認為,波音沒有在新飛機上投入巨資,反而選擇榨干已有機型平臺的做法,“是在走麥道的老路”。
“麥道是怎么從世界第二掉到世界第三,最后被波音兼并的?”Alex告訴《棱鏡》,“當年麥道推出的DC-10市場反響很好,但他們幾乎沒有怎么花錢就把它升級成了MD-11,這是一場災難,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MD-90/95身上。”
波音沒有吸取麥道失敗的教訓,2011年8月正式對外推出737Max,在一年多時間里拿下上千架訂單,確保了未來多年的現金收入。
在那之后,相似的一幕再次發生,波音于2013年再次宣布進行股票回購,直到2019年3月之前,累計回購金額超過430億美元。
“如果公司把現金浪費在股票回購上,那么它會喪失理解和提升組織能力的機會,而這些能力恰恰是生產一款安全且高效飛機所必須具備的。”Lazonick認為。
更危險的是失去未來
波音不僅在新飛機上的研發投資減少了,在合并麥道的20多年時間內,真正推出的全新飛機只有波音787一款。
“以哈里為首的董事會要求將787的大部分零部件外包給合作伙伴,這在過去的麥道是十分普遍的,但對于波音來說是第一次。”Hamilton對《棱鏡》表示。
在上個世紀90時代進行的波音777項目中,70%的零部件生產由波音自己組裝完成。到787項目,70%的零部件都是由外部供應商生產組裝。換句話說,波音在削減供應鏈縱向一體化上的投入。
“這是一條自己投資最少的道路,選擇讓合作伙伴投資,最后導致的結果是787開發成本嚴重超支,而且比原計劃晚了三年才開始交付。”Alex對《棱鏡》表示。
與787相比,737Max的連續墜毀對波音在財務上造成的損失更為慘重。
根據波音發布的最新財報,公司2019年出現了自1997年以來的首次虧損,凈虧損達到6.36億美元,并且還透露737Max全球停飛的成本高達146億美元。此外,為了緩慢重啟Max的生產,2020年還將增加約40億美元的費用。
比失去利潤更危險的是失去未來。
在推出波音787和737Max之后,波音一直在謀劃推出一款中等規模的全新機型(New Midsize Aircraft,簡稱NMA),從而彌補787和737之間的市場空白,但董事會一直沒有拿定主意。
“波音猶豫的時間太長了,以至于這塊蛋糕現在被空客搶走了。”Alex說。
在2019年舉行的巴黎航展上,空客正式推出A320家族中最大成員A321XLR,這款飛機的飛行里程可以達到4700海里,最多可以容納244名乘客,相比之下,波音737Max系列中沒有能與之匹配的競爭產品。
截止到2019年年底,空客這款飛機在全球獲得的承諾和意向訂單超過450架。
Leeham公司總經理Hamilton認為,在新飛機的研發上,波音猶豫的時間越久,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就會更加被動。
“波音是時候重新考慮自己的戰略了,但他們需要考慮的是整個產品線,考慮未來30年的發展,然后進行明智的投資,如果不這么做,他們最后的結局有可能和麥道一樣。”Alex說。
當下,737Max復飛仍是波音的“頭等大事”。根據FAA(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年初的表態,737Max最快將于2020年中復飛。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棱鏡”(ID:qqfinance),作者:羅松松,原標題:《只有利潤,沒有繁榮:波音空難一周年啟示 | 棱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