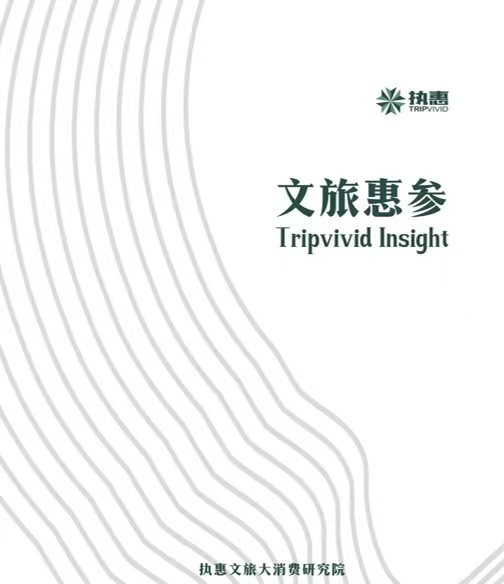新用戶登錄后自動創建賬號
登錄
疫情之下,中國飯店協會通過調研全國28個省市區600多家住宿企業發現,今年前兩個月,住宿企業營業損失超670億元,預計全年營收將同比下滑24%,共計損失在1300億元左右。
對曾經風生水起的大理民宿業來說,考驗更顯嚴酷。
“再熬一下就好了”,進入2020年以來,這是高興(化名)經常拿來安慰自己的話。從1月份講到現在,她自己都麻木了。訂單只出不進,兩個多月沒開張,“昨天有流水,2800塊。”這也是她一季度以來為數不多的收入。
一季度,本是大理民宿業主營業旺季,但今年,大家的收入約等于零。
僅春節期間的歇業,大理馬燈客棧的馬老板就損失了五、六萬元,他把希望寄托在暑假旺季,但同時也做了最壞的打算,“國慶后才恢復正常”,那個時候,他的損失在20萬元以內。
馬老板也想過撤離,在他看來,榮光已經停留在舊時光里,突如其來的疫情將加速大理現有民宿行業格局的瓦解。逃離成為大家的第一反應,但找不到合適的接盤俠,離開會很不甘心。
前途依舊未卜。
無力的自救
“才村小院,5間房,還有一間商鋪,門口就是洱海,房東直租”,“古城6間房,精致裝修位置極佳、付款方式靈活,有想法的老板聯系我”,“果子園9間房客棧,原房租轉租,有意私聊”……為了抱團取暖,大理民宿業主們建了一個群,如今,這個群淪為信息拋售群。
轉租、承包,轉讓,民宿業主們希望有人能夠分擔風險。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發現,不時有人在群里詢價,比如對于前述果子園9間房客棧,有人咨詢后,認為6.6萬元的年租金偏貴,即使老板強調是拎包入住。

民宿業主群的轉讓信息,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小郭是2019年接手一家有著16間房的海景民宿,在海東,民宿臨洱海,中間隔了一條馬路,雖然能看到海,但白天比較吵。因為是現成的民宿,相當于承包,一年房租27萬元,平均下來每個月的租金是22500元,加上雇兩個包吃包住阿姨的工資6200元,布草費、電費約2000元,每個月的成本在3萬元左右。
暑假、十一、春節、清明等時節都是大理的旅行旺季,按照民宿經營規律,一般情況下,每年的固定支出都會在這幾個階段賺夠,其它時間的收入就是凈利潤了。
但還沒等小郭回神,疫情不期而至,一下子加重了小郭的負擔。阿姨請不起了,沒有客人的時間,他盡量縮減一切開支。之前四年開民宿賺到的錢開始往外“吐”,以此補貼租金和水電等必要支出。“感覺每一天曬到自己身上的陽光都特別的昂貴,真正體會到曬太陽是件奢侈的事情。”小郭無奈吐槽。
一季度已過,盡管大理市政府已經允許營業,“沒有客人,這個時間節點上不敢亂動。”小郭對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說。
民宿業主們為了自救,開始尋找想辦法回籠資金——轉讓、轉租。
規模大的,一間一間或是一層一層的長租,規模小的整個院子按年轉租,價格也從700元/月到4000、5000元/月不等,“至少有些資金回籠,不然就是干賠著”。但外地人進不去,本地人不會接,依舊有價無市。
抗壓能力強的業主,土地的租金早就交齊,特殊時期只能減少支出生熬,唯一的期盼就是疫情趕緊過去。一部分資金雄厚的業主,則開始運用各種互聯網短視頻平臺,進行直播。他們期望利用無人的空檔時間更多的種草,在旅游行情恢復時,收獲客人。
一場疫情,迅速將“詩和遠方”打回到骨感現實。
千萬投入曾一年半就收回
從一個中轉站、落腳點,變成很多人心中的“詩和遠方”,大理只花了幾年時間。
大理最早出現的民宿,是2000年前后由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建造的月亮宮和太陽宮,以及后來陸續建造的青廬、海地生活、白居,它們成為第一批大理海景民宿代表。
2010年以前,雙廊登記在冊的客棧不過45家。2012年,大理洱海的海景民宿呈現爆發式增長,形成了海景民宿集群,被《云南日報》定義為“大理旅游轉型升級的重要載體”。2014年,電影《心花路放》上映后,大理的知名度更是達到空前的高度。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慕名打卡的游客越來越多,民宿也越開越多。
其實,大理不止有洱海,還有蒼山、古城,充沛的陽光,“蒼山不墨千秋畫、洱海無弦萬古琴”的風景,是“詩和遠方”的真實所在。
于是,來到大理開民宿的人越來越多:每天睡到自然醒,和狗子一起曬太陽,一院子的花花草草,這里的色彩永遠是絢爛的,藍天、白云、滿眼的紅黃藍綠赤橙紫,此外,喝茶聊天數錢數到手軟。
高興是大理高光時刻的受益者。
2014年,還在南方某知名媒體工作的她相中了雙廊的一塊地,簽完租約,一口氣付了18年地租,就開始籌錢設計民宿。一年后,她辭去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民宿的經營中。過程雖然艱苦,但好在回報率對得起她的付出,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把500萬投資成本收了回來。
不僅是高興,投資千萬的“無舍”老板老K,2014年營業,1年半后就收回了成本。
“那個時候生意也是真的好,一間海景房旺季能賣到上千元,海景民宿的全年平均入住率達到了75%以上。”高興對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回憶,“經常一房難求”。要知道,2015年時,只有800戶人的雙廊村就有426家民宿。
后來的生意就沒那么好做了,越來越多的民宿陸續建起。“整個環洱海圈的129公里海岸線上有2000多家。”大理客棧協會會長李海忠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在大理古城和環洱海圈里,注冊在案里的民宿客棧超過3600家。在OTO平臺上,對外銷售的民宿客棧超過7900家。

民宿熱度2018年下降,價格上揚,但大理民宿均價下滑
整個大理,遍布各式各樣的客棧和民宿。
“開始變得和麗江一樣了,極其濃厚的商業氛圍。”馬燈客棧馬老板認為,大理最后的高光時刻停留在2015年。
被摧毀的“詩與遠方”
事實上,隨著各種資本進入,大理早已不是人們心中的理想之地。
2012年,人民路上的租金只要1.8萬元一年,如今,1.8萬元只是人民路上一間30平米民宿一個月的租金;一間普通民宿,2012年時建造價格還是200萬-300萬,到了2015年,已經漲到1000萬-2000萬……民宿的回本周期也從最初的1-2年,變為4-5年。
最沉重的打擊,來自2017年開始的為期近兩年的洱海整治。
當年,環洱海的1806家民宿都在整治范圍內,違章部分全部拆除。直到2019年,陸續通過驗收的民宿,在辦理齊全相關證件之后,開始營業。此時,得以重新開張的民宿規模不足原來的一半。
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發現,這一期間,洱海邊較為知名的《心花路放》云渡、《后海不是海》洱朵、美式風格的下沫88、嘲風、喜再、隱漫、寬海、沐村、莫舍、桃源人家等,都已經消失不見。
民宿減少,游客也來的少了,大理海景民宿主們面對的是住不滿的窘境。“我之前每天的營業額有2萬,現在也就幾千。國慶節即便沒加價,也還是沒住滿。”大理三家民宿老板秦樹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2018年的情況,“以往的國慶黃金周,房價通常上漲20-30%”。
本來元氣大傷的大理民宿業,又遭遇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理民宿業主們再迎沉重打擊。
“即使沒有疫情,大理的民宿業發展已經到了瓶頸期。”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前民宿業主告訴無冕財經特約研究員,“政府沒有好的發展思路,沒有引導政策,肯定干不過其他地區。”
持有這樣觀點的人不在少數。《人民日報》曾在2018年發文指出,“大理的民宿,太不具有參考性。江浙滬民宿正以驚人的速度形成方法論,而大理民宿卻面目模糊,基數龐大,難以分類。”
大理面對的困境不僅有自身定位不精準,還有來自國內同行的強大競爭。來自民宿短租預定平臺途家網2017年數據顯示,民宿發展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是成都、北京、上海、重慶、廣州、西安、廈門、三亞、杭州和麗江。大理早就不在前十之列。
而為了激勵本地民宿業發展,各地政府紛紛出臺利好政策。
重慶南川區為了發展民宿業,推出了“以用地的形式為民宿業主確認產權”的政策;浙江松陽為激勵旅游民宿業發展,積極促成當地基礎設施建設,還給予真金白銀的現金獎勵;浙江省政府更是《民宿基本要求與評價》,對民宿行業進行規范;西安2019年出臺方案,西安市財政每年從旅游發展專項中安排資金用于支持民宿發展。
在骨感的現實中,大理的“詩和遠方”失去了色彩。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無冕財經”(ID:wumiancaijing),作者:徐英,原標題:《大理民宿業“冰凍”:徒勞的自救?|| 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