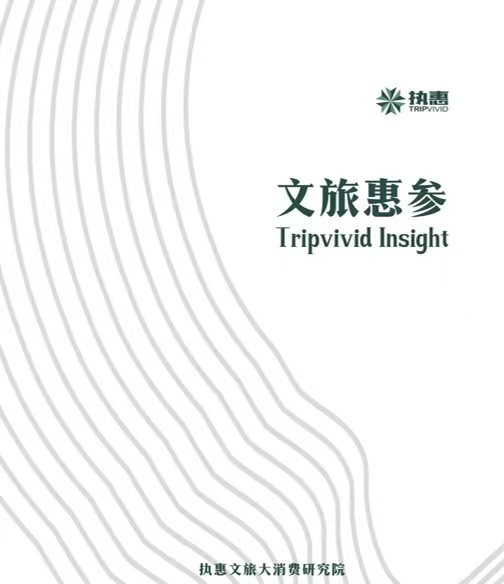新用戶登錄后自動創建賬號
登錄
5月5日,由江蘇省宣傳部、江蘇省文化和旅游廳、揚州市人民政府等單位主辦的“大運河文化旅游產業投資合作論壇”在揚州舉辦。戴斌院長應邀出席并為大會做主旨演講,全文如下:
同志們,朋友們,下午好!
我承認如下觀點,可能會讓人感到不適,但還是愿意將它作為這篇演講的出發點:我們不可能將所有的文化遺產都加以活化和利用,有的甚至連保護和保存的必要都沒有。雖然無論見過去偉大如秦皇、漢武、孔子、李白,還是見當下平凡如你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獨特,其生命過程都值得被記憶。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絕大多數人或苦難或輝煌的生命印跡,終將無聲無息地隨風而逝。在數千上萬年的歷史長河中,只有少數人的名字、思想、事功及其物化空間才有可能為歷史所記憶,化為人類文明浩瀚星空的一粒微光。參訪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時,兩個場景至今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其中,世界各地的主流報紙,定格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同一天的頭版,一張接著一張繞壁陣列,無聲講述著那么多國家和地區在同一時間發生的不同故事的同時,一束背光打在地上,光影相間幻化而成文字,Earth to earth, Dust to dust(塵歸塵,土歸土),觀者安寧如黎明前沉睡的大地,間有呼吸如枯葉自枝頭飄零。
對于京杭大運河這樣的浩大工程,也即歐美紀錄片Mega里所言,一旦失去了其本來意義上的軍事、交通、政治功能,除非有重大事件賦予其全新功能,否則只能作為人類文化遺產加以保存,是很難再現曾經的繁華的。在山東“運河之心”的論壇上,我曾以《繁華不只為追憶》做過主題演講。作為后來者,我們會記住歷史,珍惜祖先的榮耀,因為那是來時的路標。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關注當代人對當下幸福的追求,以及對未來的本真訴求。影響一代人的朦朧派詩人舒婷過三峽眺望神女峰時,石破天驚地寫下過這樣的文字,“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的肩頭痛哭一晚”。從那時起,國民生活的精神指向就不再只是承載過去的神圣榮光,而是高舉人文的旗幟,理直氣壯地追求個體的、現實的與世俗的幸福。不理解這個文化心理的嬗變過程及其內在邏輯,就無法有效建構四十年來包括文化和旅游在內的經濟社會發展歷程,也無法確認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價值尺度,更無法完整理解“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中國夢的完整內涵。回到現實,地方、社區和企業不能因為建設和發展,而隨意破壞老祖宗留下的優秀文化遺產,也不能以保護的名義無限擴大遺產的范圍,而漠視當代人發展和創新的權利。
也正是從人本主義范式,而不是文物技術和法律條文出發,我和中國旅游研究院的同事年初對《文物保護法》的修訂提出了如下的觀點。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但是人民不可能只守著記憶活著,無論這些記憶是逝去的繁華,還是曾經的苦難。以前我們對文化遺產搶救不夠,保護不夠,所以要建立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文化公園等制度體系,通過國民教育、科學研究、群眾文化、紅色旅游等途徑加以傳承,這些工作仍需要堅持做下去。與此同時,面對人民對文化遺產的參與度和獲得感不足的現實課題,我們還需要平衡好保護和利用的關系。既要守住意識形態的底線,防止被市場牽著鼻子走,甚至為票房而戲說歷史、歪曲歷史;也要避免無視社會發展和人民需要,而出現類似于文化保護原教旨主義的傾向。事實上,在文化遺產的功能重構和價值實現的過程中,文化人和旅游人都應該走出相對封閉的小圈子,走向社會,走向大眾,借助一切可能的平臺、渠道和方式,傳承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生產高品質的文化內容,滿足人民對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
同志們,朋友們,
價值是由需求定義的,需求越多,市場基礎越厚實,價值越大,反之則反是。現在有一種傾向,一說文化資源開發和遺產活化,就奔著旅游市場和產業方向去。事實上,旅游是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化的重要領域,但絕不是唯一的領域,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領域。世居于此的城鄉居民和常住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才是文化建設的主要服務對象,也是創新發展的源動力。經常會聽到這樣的數據,本地常住人口數十、數百和上千萬,年接待游客數百、數千萬,甚至數億,并且得出結論旅游市場規模是本地居民的十倍之多。卻沒有意識到本地市場可是常住居民一年365天,一日三餐高頻消費堆積而成,而旅游市場是游客長則數周,短則一天的低頻消費拉動的。沿著這個思路,文化為誰而建,遺產為誰而活的問題不就容易理解了嗎?我們面對近在咫尺的市場需求,固然需要引進外來的資本、技術和專業人才,但更要重視本土企業和人才在文化創意、創業、創新和創造方面的天然優勢。與物質生產不同,涉及文化建設和生活品質的提升,不可能也沒必要動不動就搞什么產業園、什么大工程。揚州是文化的、歷史的、世界的,更是生活的、當代的和揚州人民的。當且僅當揚州人民的生活幸福了,異國他鄉的游客才會愿意到訪,才會滿意而歸。
大運河及其所承載的漕運、官渡,還有乾隆下江南,都是流動的文化,所有的重點都在水和船,在人與水的交融。不要總想著在城市中建靜態的博物館,可不可以放寬視野,依托運河建個水上博物館,既承載歷史記憶,也展現空間的流動?多數情況下,單純的靜態展示,就靠現在的一些老照片,連個場景和物件都沒有,加上乏味的解說,是很難引起人們共鳴的。只有深深植入本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把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建到社區中去,讓文化活動和藝術事件像陽光、空氣和水一樣融入到日常生活場景,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公共文化的服務效能才能得到有效提升,文化強國的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我國臺灣的白先勇先生由文入戲,以己之力振興昆曲藝術,青春版、廳堂版的《牡丹亭》在華人世界常演常新。如果不是深耕于當代觀眾市場,不是持之以恒聚焦改進,而僅是一味靠保護和小圈子里的自我欣賞,恐怕取得不了今日成就吧。林懷民先生在臺灣地區創辦的云門舞集,借著“光著腳”跳的現代舞,在露天的舞臺,學校的操場,飄香的稻田,甚至榕樹下的一片空地上,卻把九歌、紅樓夢、書法等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傳遞到了社區,深植于一代年輕人的精神里。像這樣在不同文明的對話中,借助當代傳播手段,把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更多案例也都表明,文化遺產活化,需要普及、傳承和創新。而首先是普及,是要讓文化遺產走入當代生活,而非簡單意義上的收藏在博物館或立個牌子式的保護。普及還應該是開放的體系,既要重視權威和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傳播,也要重視草根和大眾的自發創作和市場擴散。QQ音樂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新生代音樂人尤長靖演繹的《西遇》上架不到一小時,評論就破萬,微博轉發量則超過120萬,當下的敦煌正因年輕群體的認同而快速傳播。LOFTER上的同人作品,同樣是因為創作者與讀者可以互動,而不是傳統的我寫你讀,才涌現不少有生命力的經典詮釋。客觀地講,文化主管部門和專業研究機構對此關注不夠,繼續下去的話,我們將無法與下一代對話。
同志們,朋友們,
價值是由投資、技術、創意、研發、生產、服務等供給體系決定的。以前去景區,到哪兒都是廉價的珍珠、貝殼、串珠和手鏈,當然需要反思和創新。現在呢?幾乎所有的歷史文化街區和博物館都在以文創的名義兜售新一輪的旅游紀念品,滿眼都是故作萌態的故宮貓、膠帶紙和手機殼。小孩子想要一把當場就可以拿著玩、瘋著跑的侍衛刀槍而不得,只能失望而歸。而對此情此景,我想問創意開發團隊,研發過程中有問過一句小孩子們真正需要什么了嗎?又或者以網紅的名義,到處梁山好漢式摔碗酒、文藝青年式留言、涂鴨、漂流瓶什么的,這不是為文創而文創又是什么?也有動不動就把“純手工”做賣點,如果純粹的手工制作就等同于文化和品質的話,那么對工業革命、科技革命、文藝復興的歷史豈不是要重新評價?我們善于借鑒和模仿,但似乎更善于把任何需要積淀、耐心和智慧的事情,弄成快速圈場子,又快速散場子的快消品。文明演化和生活幸福這樣的事情,既不可能是權威部門的規劃,也不可能是靠抖機靈的策劃,它一定是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文交流上邊際創新的結果。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紅只是文化遺產活化的第一步。
接下來是面向當代生活的內容創造和品質提升。不能一說文化就是歷史遺產和外來的高雅藝術,不能總想建標志性的博物館、藝術中心、大型主題公園,要研究當下老年人、青年人、少年兒童、學齡前兒童的閱讀、影視、戲曲、舞蹈、音樂、游戲、購物、餐飲等現實生活需求。這當然就需要公共文化機構和旅游企業面向,更需要創作團隊重歸生活場景。上海彩虹合唱團、河北他奶奶的廟等市民和村民自發形成的文化現象值得認真研究。比如世界、M&M、泰迪熊博物館等室內親子樂園的興起,及其背后的文化驅動力和市場邏輯,同樣值得研究。在文化遺產活化和當代創新的過程中,我們也要敢于利用,更要善于利用資本、技術和商業的力量。中國旅游研究院上個月在京發布了夜間旅游研究成果,明確提出了18:00—22:00“黃金四小時”的概念,良業等企業在商業實踐中形成了“光影雕刻”的產品。照明技術是驅趕黑暗,光影藝術則是重構夜晚的生活空間。這樣的技術和產品已經很成熟了,G20峰會可以用,周末的大眾休閑也可以用。廣州的小蠻腰、溫州的甌江兩岸可以用,運河沿線也可以用啊。現在年輕人的旅游休閑訴求,已經不再是簡單地吃吃喝喝、玩玩樂樂,而是帶有對知識的更高訴求。專題研討的時候,我年輕的博士團隊甚至提出了“我與運河一起重生”的構想,針對斷運的河段,建立一個支付寶螞蟻森林那樣的平臺,通過社群的努力讓斷運的人工河重生。她們還提出“動手造個船,陪你下江南”的商業創意,結合工程、數字、人工智能和時尚音樂,先把人氣聚起來,這些blingbling讓人直呼年輕人身上孕育的豐富想像力和無限可能性。沒有國民大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廣泛參與,沒有思想的引領和技術的應用,沒有企業家的商業創新,我們也許會守護歷史的記憶,卻過不好未來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還會有少數人走得更遠,他們會一直走到文化的邊緣,走到當代人思想的邊界,以高度的歷史自覺進行邊際意義上的探索與創新。這些打著“實驗”“先鋒”“探索”的名義所進行的文化活動,可能會是蒙克的《吶喊》、 梵高的《星空》、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也可能什么都不是。不過正是由于這些無法確認最終價值的創作,甚至是個體毀滅性的創造,才讓一間居所、一條街道、一座城市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記憶,成為世界文化地標。如果說呆萌的網紅隨處可見,資本和技術驅動的內容創造有跡可尋,那么走到邊緣進行邊際創新的文化活動則是我們無法預測的,更是不可規劃的。就像當代量子物理讓我們重新認識世界的不連續與不可測一樣,當且僅當一切行政的、市場的和科技的力量,在文明演化和人民生活面前保持真正的謙卑,甚至“愛,直至被傷害”,文化遺產才不止是繁華記憶,也是生機勃勃的未來。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旅游研究院”(ID:CTA20080606),本文作者:戴斌,原標題:《戴斌:文化遺產的功能重構與價值實現》。